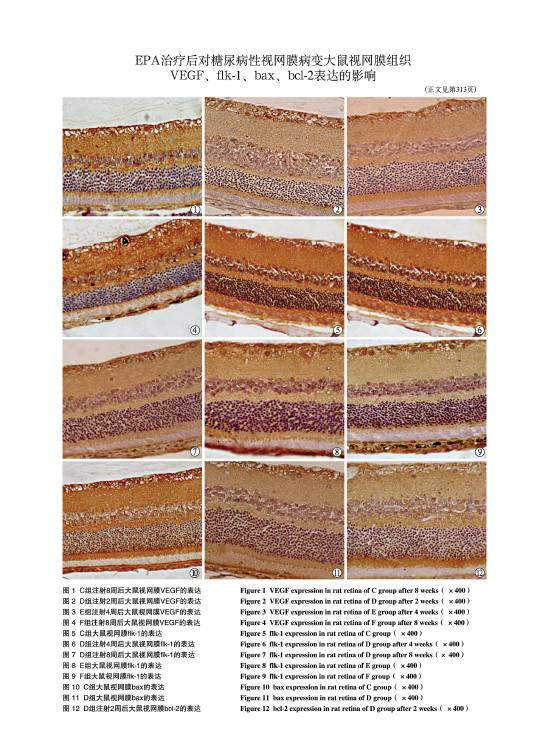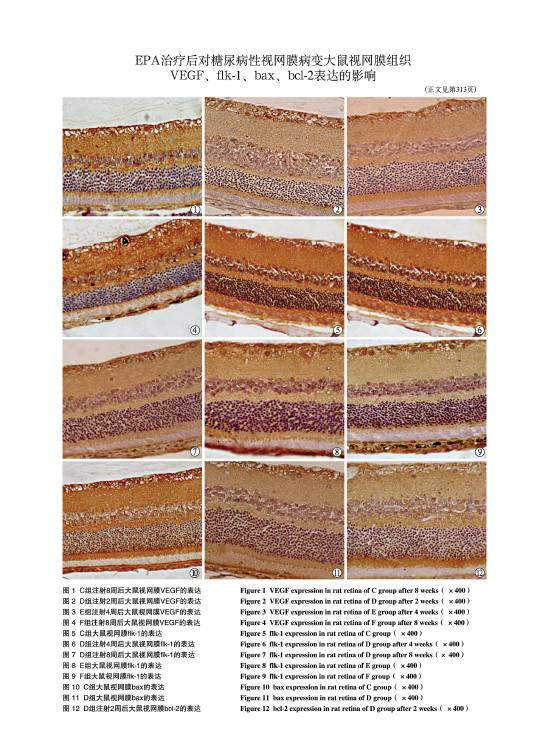
梁 敏1,2(综述),马 丽3,陈海英1*(审校)
(1.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2.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7;3.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关键词]抑郁症;嗅通路;嗅球;综述文献
doi:10.3969/j.issn.1007-3205.2018.03.030
抑郁症是一种以持久的情绪低落为特征的心理障碍,其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第二大致死原因[1]。目前临床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等。由于目前临床常用的抗抑郁药物具有易复发、不良反应大等问题,故抑郁症的治疗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嗅觉与抑郁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嗅觉作为唯一一种大脑直接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感觉,不仅在母乳喂养、寻找食物、预测威胁、调节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可以影响个体的情感变化,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以及治疗。因此,探索嗅觉与抑郁症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出现。现就嗅觉通路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进行综述,旨在寻求通过嗅觉途径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
抑郁症是一种以持续性显著性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科疾病,主要表现为快感缺乏、兴趣丧失,常伴有焦虑、无价值感、思维迟缓、记忆力下降、言语减少、饮食睡眠差、自觉全身多处不适等症状,严重者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目前抑郁的发病机制尚无统一定论,但存在多个假说。
1.1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 是最经典的抑郁症发病机制假说,该假说认为抑郁症主要是由于脑内突出间隙单胺类神经递质如5-羟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多巴胺(dopamine,DA)、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等缺乏所致。此外,单胺类神经递质还包括乙酰胆减(acetylcholine,Ach)、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等。动物实验显示抑郁模型组大鼠在表现出抑郁样行为的同时脑内5-HT、NE和DA水平显著下降,但伴随着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其水平也会出现显著的升高[2-4]。而该研究结果同样存在于抑郁患者身上。基于这一理论,临床一线抗抑郁药多选用单胺类神经递质再摄取抑制剂如选择性5-HT再摄取抑制剂(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SRI)。该类药物在临床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表现出不足之处如起效较慢、存在不良反应、部分患者对该类药物不敏感等。可以明确的是单胺类神经递质确实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单胺类神经递质假说不是抑郁症发病的唯一机制。
1.2神经发生假说 是抑郁症发生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假说,特别是海马的神经发生与抑郁症密切相关。该假说认为长期慢性的压力会导致海马神经元的损伤和减少[5],而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则可以促进海马神经元的再生[6]。这一过程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BDNF具有促进神经细胞增殖、重塑、生存等重要功能。在1995年Nibuya等就发现在抗抑郁治疗之后BDNF的水平发生变化,随后BDNF在抑郁症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研究。动物研究发现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可以明显增加海马BDNF的水平[7],促进海马神经元的发生。
1.3神经炎症假说 神经炎症是目前抑郁症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长期慢性炎症是众多压力诱导型疾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是抑郁症的重要影响因素。炎症反应在压力诱导抑郁症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8]。临床研究发现,抗炎药物可以产生抗抑郁的效果[9]。动物实验中,促炎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在抑郁动物模型体内的水平显著升高,这一研究结果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同[10]。而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同时可以扭转炎性因子水平的升高。目前已经得到认可的抑郁动物模型建造方法如注射内毒素建造抑郁动物模型,便是基于此理论。抑郁症的神经炎症理论与难治性抑郁症存在密切联系,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可能会带来抑郁症临床治疗的新进展。
1.4其他假说 不仅如此,抑郁症发病机制还包括神经内分泌紊乱假说、兴奋性氨基酸中毒假说等。此外,中国古代医学也对抑郁症的发病机制进行了阐述。抑郁症在中医理论中属于“郁”证的范畴,郁证是指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致,是以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胸部满闷、胁肋胀痛,或易怒喜哭,或咽中有异物梗塞等症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证。其发病原因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外生诸邪如外感六淫,寒热交替的变化等引起内外失和而积聚于体内,或是厚食肥甘、当化不化、停滞不通,久而成火、痰、湿等,则生郁证。二是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血津液代谢异常,痰、湿等滞留于体内,形成郁结;三是由于情志内伤、七情不及或太过,引起五脏气机壅滞,升降失常。由此可见,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的多个假说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在抑郁症的治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正是由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未统一和明确,临床抑郁症的治疗仍不能满足所有抑郁症患者的需要。因此,对抑郁症发生机制的深入研究依然是该研究领域的难点和重点。
2.1嗅觉通路对抑郁症的影响 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嗅上皮的损伤可以诱导抑郁行为,故使用硫化锌损伤昆明鼠嗅上皮可以作为制备抑郁动物模型的方法。除了动物实验,临床研究也表明,失去嗅觉的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产生抑郁,如慢性鼻窦炎患者就具有更高的抑郁症发生率[11]。并且研究发现失去嗅觉的患者中出现轻度抑郁症状者大约达1/3[12]。
嗅球作为嗅觉处理的初级中枢,参与嗅觉的处理过程。嗅球的体积会影响嗅觉功能,在研究中发现嗅觉能力与嗅球体积相关。嗅球将气味信号同时扩散至除嗅觉处理中枢外的其他脑区,参与抑郁等情感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嗅球摘除后,动物体内5-HT和DA含量出现改变并伴随出现抑郁样行为[13]。因此,嗅球摘除可以用来制备抑郁动物模型[14],这一抑郁模型可以引发抑郁样行为,同时能够引起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的变化,而且临床抗抑郁治疗方法可以对抑郁状态进行有效的扭转。人类也一样,嗅球结构缺失会增加抑郁风险。相反,有严重抑郁症的患者也会出现嗅球体积减小。由于嗅球体积的变化主要发生在童年时期,故在抑郁症患者中,童年经历过创伤的患者较没有经历过创伤的患者嗅球体积减少20%[15]。这表明,无论是先天或后天的嗅觉缺陷还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嗅球损伤或减小均对抑郁症的发生起到影响作用。
2.2抑郁症对嗅觉的影响 抑郁的患者也会出现嗅觉障碍,研究表明嗅觉障碍常出现在各种精神疾病之前[16],这种临床现象有可能发展成为精神病发生的警报。抑郁症患者会出现嗅觉阈值、嗅觉辨别和嗅觉识别能力的下降。回顾性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与非抑郁症患者的嗅觉功能存在显著差异[17]。同样的情况存在于抑郁的动物模型中,抑郁模型的小鼠会出现明显的嗅觉记忆障碍[18]。在经历慢性不可预见性应激之后出现抑郁样行为的大鼠也同时存在嗅觉功能的下降[19]。并且抑郁模型组大鼠与对照组相比嗅上皮变薄、嗅觉感受器神经元减少、嗅球凋亡增多[20]。这可能表明抑郁症损伤了嗅觉信息的处理,降低了嗅觉感受器的工作效率,也有可能是抑郁状态使个体减少了对气味的注意。不仅仅是抑郁症,其他神经精神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21]、阿尔茨海默病[22]、帕金森[23]等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嗅觉功能损伤。反之,有效的抗抑郁治疗则会扭转嗅觉能力发生的损伤。
2.3嗅觉通路和抑郁症相互影响的中医理论 中国古代医学中的“百合病”、“脏躁”、“不寐”等均属于抑郁症的范畴。中国古代医学对抑郁症和嗅觉的联系早有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在将嗅觉刺激应用于抑郁症治疗。无论是中国古代医学还是现代医学使用嗅觉刺激治疗抑郁症的研究多选用芳香类药物及其提取物,此种方法属于中医芳香疗法中的一种。抑郁症的中医发病机制存在多种说法,中医认为“五脏主五志”,而心、肝、脾与抑郁、焦虑等联系更为密切。在抑郁症的中医证候分布中也以肝郁脾虚、心脾两虚最为多见。从肝论治、肝主疏泄主要是指肝具有使本脏以及其他脏腑功能的气机流畅的作用。而肝失疏泄则导致气机阻滞、胸胁胀满。而芳香药物具有性温、味辛、气香,归脾经胃经,次入肝经肺经,升散走窜的特点,能疏畅气机、宣化湿浊。因此,芳香药物以其辛香升散之性、调畅气机、理气行气,使气机条达通畅、肝复疏泄,从而改善郁证气机壅滞、心情抑郁的症状。从脾论治,脾在五情主思,思虑太过易伤脾气,影响脾的运化功能,导致水湿内停积聚,加上脾喜燥恶湿的特性,湿邪侵犯人体,最先困脾,损伤脾阳,导致运化失常。芳香药物,辛温香燥,健脾化湿燥湿,辅助改善脾胃功能,调畅气机,祛除病理产物,改善郁证。从心论治,心藏神,郁久伤心。芳香药物既可开心窍、宣散气血津液瘀滞,又可通九窍、上达巅顶、通透脑腑。由此可见,嗅觉刺激通过芳香物质的升散走窜、辛温燥湿及开窍等作用达到肝复疏泄、健脾化湿和开心窍的效果,从而缓解抑郁症状。以上的综述表明嗅觉的能力和嗅觉器官的完整性与抑郁等情绪存在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这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2种症状相关性方面的初步探讨,而抑郁症与嗅觉相互影响的具体途径和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嗅觉属于化学感觉,是由于气体物质刺激嗅觉感受器而产生。嗅觉系统的形态学包括嗅上皮、嗅球和嗅皮质。嗅觉系统的一级神经元就位于鼻腔的嗅上皮(也称嗅黏膜)上,嗅黏膜是由嗅觉细胞、支持细胞和基底细胞组成,其中嗅觉细胞就是嗅觉的感受器。气体分子通过呼吸气流到达嗅黏膜或者通过吞咽食物进入咽部再到达嗅黏膜与嗅觉细胞结合,嗅觉信号沿着细胞突出传达至嗅球,嗅球是嗅觉信息的重要中转站,嗅球包含3种神经元:僧帽细胞、刷状细胞和颗粒细胞。僧帽细胞和刷状细胞是嗅球上主要的二级神经元,该细胞的轴突以嗅束的方式投射到初级嗅皮质即梨状皮层和内嗅皮层等。次级嗅皮质接收来自初级嗅皮质的纤维,而次级嗅皮质的投射是相当弥散的。此外,嗅球也会直接投射到大脑的边缘系统。因此,参与嗅觉处理的许多中枢均同时参与情感的形成如海马、海马旁回、杏仁核等。
此外,嗅觉的传导过程还包括了以谷氨酸为代表的兴奋性神经递质和以GABA为代表的抑制性神经递质的参与,这2种递质在嗅球、嗅结节、杏仁核和中隔区有表达。而这些神经递质是参与抑郁症发生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这种抑郁症和嗅觉通路在解剖和功能上的联系为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
基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将嗅觉刺激作为治疗抑郁症新方法的探索不断出现。在动物实验研究中发现通过芳香药物的嗅觉刺激可以有效扭转抑郁样行为。香兰素可以通过嗅觉途径提高大鼠脑内5-HT、DA水平,扭转小鼠的抑郁样行为[24]。花梨木精油吸嗅可以达到与氟西汀同等的抗抑郁水平,同时提高海马、下丘脑、杏仁核DA等阳性反应产物[25]。香草醛吸嗅也可以提高小鼠血浆及海马区5-HT表达[26]。这表明不同种类精油吸嗅可以改善抑郁样行为,同时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吸嗅提高边缘系统内单胺类神经递质,如5-HT、DA的水平,从而达到改善动物抑郁样行为。另外,香草醛、香兰素以及麝香精油吸嗅均可以提高小鼠脑组织BDNF表达,改善小鼠抑郁样行为[27]。表明芳香吸嗅可以促进神经发生尤其是海马的神经发生、增强突触可塑性、促进各种神经元的再生特别是促进多巴胺能及 5-羟色胺能神经元的再生。由此可见,目前动物研究已经证实通过芳香物质的嗅觉刺激可以改善抑郁样症状。但是,现在的研究还不能证明嗅觉刺激发挥作用的途径是通过或者说仅仅通过调节上述相关物质的表达水平发挥作用。也不能确定是嗅觉刺激通过调节以上各种物质水平从而改善抑郁症状还是在抑郁症状改善之后体内相关物质水平发生相应的积极改变。
由上述研究得知将动物模型置于芳香环境中可以改善抑郁症状,但在实验过程中无法确定芳香药物是否还通过除嗅觉途径外的其他途径如皮肤吸收等发挥作用。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芳香物质是否是嗅觉通路达到抗抑郁效果。有研究对嗅球摘除或嗅黏膜损伤的抑郁模型小鼠进行同样的香兰素[24]和香草醛[26]吸嗅,均无法扭转其出现的抑郁样行为也无法提高小鼠体内5-HT和DA的水平。提示芳香物质发挥抗抑郁作用是通过嗅觉途径,而嗅觉途径损伤则无法达到治疗效果。利用生物电生理技术可以记录到小鼠在吸入丁香酚的过程中嗅球、下丘脑、海马、杏仁核等部位出现由丁香酚所诱发的特征性生物电变化。通过脑显像显示出,受试者在吸嗅芳香物质时颞叶内侧边缘系统、眶额叶皮质等情绪活动相关区域引起明显活化[28]。因此,可以发现个体在接受嗅觉刺激的过程中情绪相关脑区会发生活化,这是将嗅觉和情绪脑相联系的直接证据。
除了动物研究,将嗅觉刺激应用于临床患者的探索也取得一定效果,如将薰衣草精油应用于产后抑郁的患者可以有效改善其抑郁状态[29]。嗅觉刺激与产后按摩相结合可以使产褥期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30]。使用芳香中药枕联合耳穴贴压用于卒中后抑郁患者,发现效果优于单独使用耳穴贴压者[31]。限于临床实验的复杂性和临床治疗的需要,嗅觉刺激在临床的应用多与临床抗抑郁治疗方案相结合,或者将嗅觉刺激用于仅仅是有抑郁情绪的参与者,故嗅觉刺激的临床有效性无法得到直接的证实。加上嗅觉刺激改善抑郁症的机制尚未明确,将这一方法用于临床实践仍需要科研工作者不断的探索。
基于抑郁症和嗅觉通路在解剖结构、生理功能和病理改变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将嗅觉途径用于治疗抑郁症的不断探索,有望寻求出通过嗅觉途径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但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以便为嗅觉途径治疗抑郁症的临床应用提供切实可靠的证据。
[参考文献]
[1] Kessler RC,Bromet EJ. The epidemiology of depression across cultures[J]. Annu Rev Public Health,2013,34:119-138.
[2] Chen Y,Xu H,Zhu M,et al. Stress inhibits tryptophan hydroxylase expression in a rat model of depression[J]. Oncotarget,2017,8(38):63247-63257.
[3] 彭彬,刘仲华,林勇,等.L-茶氨酸改善慢性应激大鼠抑郁行为作用研究[J].茶叶科学,2014,34(4):355-363.
[4] Khnychenko LK,Yakovleva EE,Bychkov ER,et al. Effects of fluorencarbonic acid derivative on the levels of monoamines and their metabolites in brain structures of rats with modeled depression-like state[J]. Bull Exp Biol Med,2017,163(5):632-634.
[5] 成翔,张蕾,姚莉红,等.慢性应激抑郁状态对大鼠海马神经元再生的影响[J].神经解剖学杂志,2013,29(4):431-434.
[6] 梁佳,李卫东,吴元坪,等.电针对慢性应激抑郁模型大鼠海马神经元凋亡与再生的影响[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4):947-950.
[7] Bedel HA,Kencebay MC,Ozbey G,et al. The antidepressant-like activity of ellagic acid and its effect on hippocampal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levels in mouse depression models[J]. Nat Prod Res,2017[Epub ahead of print].
[8] Liu YZ,Wang YX,Jiang CL. Inflammation:The common pathway of stress-related diseases[J]. Front Hum Neurosci,2017,11:316.
[9] Kohler O,Benros ME,Nordentoft M,et al. Effect of anti-inflammatory treatment on depression,depressive symptoms,and adverse effect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J]. JAMA Psychiatry,2014,71(12):1381-1391.
[10] Wu S,Gao Q,Zhao P,et al. Sulforaphane produces antidepressant- and anxiolytic-like effects in adult mice[J]. Behav Brain Res,2016,301:55-62.
[11] 冯娟.慢性鼻-鼻窦炎术后复发相关因素探讨及心理学特征与手术疗效分析[D].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16.
[12] Croy I,Nordin S,Hummel T. Olfactory disorders and quality of life--an updated review[J]. Chem Senses,2014,39(3):185-194.
[13] 何敏,刘金伟,龚锡平,等.逍遥散对嗅球摘除抑郁模型大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研究[J].中药药理与临床,2014,30(5):14-17.
[14] Depciuch J,Parlinska-Wojtan M.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nges in phospholipids and proteins investigated by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in olfactory bulbectomy animal depression model[J]. J Pharm Biomed Anal,2017,148:24-31.
[15] Croy I,Negoias S,Symmank A,et al. Reduced olfactory bulb volume in adults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J]. Chem Senses,2013,38(8):679-684.
[16] Kamath V,Turetsky BI,Calkins ME,et al. Olfactory processing in schizophrenia,non-ill first-degree family members,and young people at-risk for psychosis[J]. World J Biol Psychiatry,2014,15(3):209-218.
[17] Taalman H,Wallace C,Milev R. Olfactory functioning and depression:a systematic review[J]. Front Psychiatry,2017,8:190.
[18] Cook A,Pfeiffer LM,Thiele S,et al. Olfactory discrimination and memory deficits in the flinders sensitive line rodent model of depression[J]. Behav Processes,2017,143:25-29.
[19] Raynaud A,Meunier N,Acquistapace A,et al. Chronic variable stress exposure in male Wistar rats affects the first step of olfactory detection[J]. Behav Brain Res,2015,291:36-45.
[20] Li Q,Yang D,Wang J,et al. Reduced amount of olfactory receptor neurons in the rat model of depression[J]. Neurosci Lett, 2015,603:48-54.
[21] Kiparizoska S,Ikuta T. Disrupted olfactory integration in schizophrenia: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tudy[J]. Int J Neuropsychopharmacol,2017,20(9):740-746.
[22] 于焕新,杭伟,张金玲,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嗅觉功能以及嗅球体积和嗅沟深度的研究[J].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15,29(5):444-447.
[23] 余凤,黄丽玉,叶钦勇,等.帕金森病患者的嗅觉功能评价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16,42(7):395-399.
[24] 刘扬,许慧,徐金勇,等.香兰素吸嗅对大鼠抑郁样行为及脑单胺类神经递质的影响[J].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2014,31(7):606-609.
[25] 陈军,徐金勇,徐蓉,等.花梨木精油通过嗅觉通路改善小鼠抑郁样行为及其神经递质[J].江苏医药,2012,38(6):657-659.
[26] 王艳梅.香草醛吸嗅改善C57小鼠抑郁样行为及其机制的探索[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3.
[27] Ayuob NN. Evaluation of the antidepressant-like effect of musk in an animal model of depression:how it works[J]. Anat Sci Int,2017,92(4):539-553.
[28] 杭天依.芳香物质经嗅觉通路激活人脑区的影像学观察[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3.
[29] Kianpour M,Mansouri A,Mehrabi T,et al. Effect of lavender scent inhalation on prevention of stress,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the postpartum period[J]. Iran J Nurs Midwifery Res,2016,21(2):197-201.
[30] 梅珊珊,张广兰,秦爽,等.芳香疗法联合产后康复按摩对产褥期心理状态的改善作用[J].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4,14(24):4737-4740.
[31] 汤娟娟,王俊杰,桑丽清.芳香中药药枕联合耳穴贴压对卒中后抑郁患者的效果观察[J].中华护理杂志,2015,50(7):848-851.
[收稿日期]2017-12-12;
[修回日期]2018-01-10
[作者简介]梁敏(1993-),女,河北邢台人,河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医学硕士研究生,从事临床护理学研究。
*通讯作者。E-mail: hychen1964@163.com
[中图分类号]R749.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205(2018)03-0368-05
(本文编辑:许卓文)